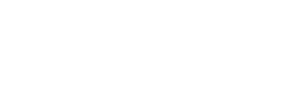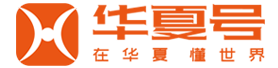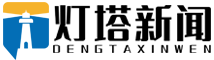紫柏山麓话张良
■ 史飞翔(陕西)
冬日暖阳,车行留坝。青苍如墨,漫向天际。紫柏山麓的张良庙,黛瓦红墙隐于松柏翠影之间。立于山门,举目望去,“汉张留侯祠”五个朱红大字赫然矗立。两侧有一联:“博浪一声震天地,圮桥三进升云霞。”
步入庙内,有一佳处,名“北花园”。园之西南有一六角班爪形亭阁,曰“拜石亭”。亭内有方形石桌,鼓形石凳、石几。正墙嵌有明代赵贞吉的《怀山好》词。亭柱上有于右任草书楹联“不从赤松子,安报黄石公”。亭前立有“英雄神仙”巨碑。
“英雄神仙”四字,是中国人最极致的人生理想,却也是最难抵达的彼岸。秦末烽烟里的张良,本是韩国贵族子弟,国破家亡之恨如利刃悬颈,他散尽千金寻刺客,于博浪沙掷出铁椎,试图以一己之力撼动暴秦根基。结果铁椎误中副车,秦始皇侥幸躲过。无奈之下,张良只好亡命天涯。彼时的他,是乱世棋局里一枚孤勇的棋子,怀揣着英雄梦,却只能在大时代的洪流里窥见个人的渺小。这份壮志难酬的无力,是命运赐予他的第一道痛彻。
幸遇黄石公,得授《太公兵法》,使得张良成为刘邦麾下“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”的第一谋臣。鸿门宴上巧计脱险,谏止复立六国以绝后患,邀四皓出山稳固太子之位,张良以谋略照亮汉室江山来路,封侯万户,荣光加身。此刻的他,是朝堂之上名副其实的英雄,恰如“英雄神仙碑”所镌,站在了入世功业的顶峰。可越是身处繁华之巅,张良越能嗅到功高震主的危险气息。萧何入狱,韩信殒命长乐宫钟室,昔日同袍的鲜血染红宫墙,帝王的猜忌如蛛网密不透风。这种伴君如伴虎的惊惧,是命运赐给他的第二道痛彻。
赵贞吉笔下的《怀山好》,恰是张良心灵轨迹的最好诠释。明隆庆五年(1571年),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因朝中权力倾轧,被迫告老还乡。途中经过此地,触景生情,写下这篇词作,后刻石留存,与“英雄神仙碑”遥遥相望,为解读张良的精神世界,写下了穿越时空的注脚。
“紫柏山前车马道,道上红尘灭飞鸟”,寥寥十四字,道尽了仕途的喧嚣。那车马往来的官道上,滚滚红尘浓烈得连飞鸟都难以穿越,一如张良身处的朝堂,权力的漩涡足以吞噬一切。“尘里行人不知老,嗟来几度怀山好”,世人在功名利禄的泥沼里奔波,浑浑噩噩间耗尽一生,待到幡然醒悟,才惊觉隐居避世的志向,早已被岁月磨蚀。而“年少怀山心不了,年老怀山悔不早”,更是赵贞吉结合自身仕途坎坷的喟叹——年少时心怀山林,却被俗世功名牵绊;垂老之年看透虚妄,才悔恨归隐太迟。赵贞吉的这份悔恨,恰恰反衬出张良的智慧。当刘邦的猜忌渐生,当“狡兔死,良狗烹”的阴影笼罩汉初三杰,张良读懂了红尘的险恶。他毅然向刘邦请辞:“愿弃人间事,欲从赤松子游。”这不是一时兴起的洒脱,而是历经生死后的清醒。他舍弃万户侯的尊荣,遁入紫柏山的烟霞之中,晨钟暮鼓为伴,松涛流云为友。昔日的英雄,终成世人眼中的“神仙”。
赵贞吉在诗的结尾写下振聋发聩的一句:“君不见,京洛红尘多更深,英雄着地皆平沉。”京洛的红尘,比紫柏山前的官道更浓烈、更凶险,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,最终都难逃“平沉”的结局。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,更是对张良选择的高度认同。张良的“英雄”之名,成于谋略,立于功业;而他的“神仙”之境,成于取舍,立于顿悟。他不是天生的智者,而是在命运的刀光剑影里,看透了功名的虚妄,懂得了“怀山”的真谛。
立于“英雄神仙碑”前,细读《怀山好》的刻石,我陷入沉思。“英雄神仙”这四字背后,从不是两全其美的圆满,而是痛彻心扉后的取舍。碑上的“英雄”,是张良半生的颠沛与功业;诗中的“怀山”,是他看透红尘后的归宿。赵贞吉写下这首诗时,或许正是从张良的选择里,读懂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存智慧——英雄之路,是搏命的厮杀;神仙之境,是保命的退让。二者之间,隔着血与泪的顿悟。
山风拂过,寒彻心骨。“英雄神仙碑”与《怀山好》词碑默然相对,一个刻着入世的荣光,一个写着出世的醒悟。紫柏山的草木枯荣千年,张良的精神世界,便在这两方石碑间流转千年。世人所谓的英雄神仙,从来不是兼得的完美,而是在红尘倾轧后,终于懂得“怀山好”的真谛。这份取舍背后的痛彻,才是紫柏山间最动人的人间清醒。